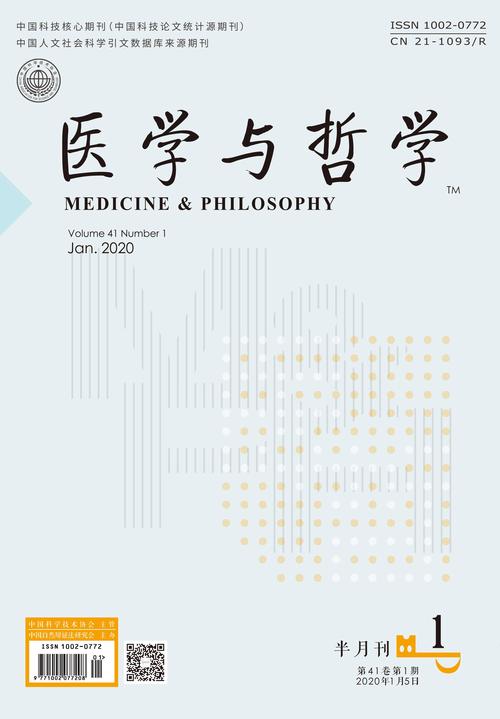
易学与哲学
易学的三大特性:变化、恒常、简洁
易学,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具有独特语言体系的专业学问;从内容上讲,是一种高度哲学化的天人之学。它不仅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宋易学家胡瑗,在其《周易口义》中提到:“《易》之道极其广阔宏大,蕴含天地间的深邃内涵,涵盖人事的始终。”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其经部易类的《小序》也曾这样评价:“《易》这本书,是通过推演天道来阐明人事的。”这些见解,极具代表性地揭示了《易》及其衍生的易学以天道与人事相贯通的天人之学的基本学术特质。只有深刻理解了易学这一学术特质,北宋易学家邵雍才能提出“不贯通天人,不足以称之为学”的著名论断。
易学起源于带有宗教巫术性质的占卜活动,后来发展为一种高度哲学化的天人之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哲学发展中非理性信仰与哲学理性之间的消长关系,以及前者的逐渐转化为后者的过程。占卜体现了古人对未来预测的强烈愿望,激发人们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前瞻视野与智慧,进而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升华出易学知来藏往的哲学基础。受此影响,中国哲学也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历史理性意识的藏往而智、知来而神的哲学。智体现智慧,神体现神妙。
变化是易学的第一要义。易学启示我们,宇宙一直在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社会人生也应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易学表明,变化之中有恒常,与变化密切相关的,就是与之相对的恒常。通过变化实现宇宙、人生中万象位置的确定,达成万象间的和谐有序、良性互动,乃至整个宇宙、人生的有序、和谐且顺畅,这是变化的最终目标。在这里,万象在整个宇宙、人生的大背景下所确定的位置,以及它们在此基础上良性互动形成的和谐整体秩序,就是不可改变的。正因为如此,追求天人合一、天人有序且和谐,人生有序且和谐,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关切。
除了变化和恒常之外,易学还有简洁的意义。《系辞下传》提到:“乾,明确地展示给人以简单;坤,明确地展示给人以简约。”乾天坤地在孕育万物的过程中,展现出简洁而不繁复、顺应自然且流畅的特质,真正领悟到这一简洁性,才能透彻理解天地、宇宙的运作原理,理解宇宙、人生的奥妙。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崇尚简约、以简驭繁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这三大特性构成了易学的基本内涵,从中已初步透露出易学天人之学的基本特质。这种特质在其三才之道学说中得到了全面展现。
易学中的三才:天、地、人
三才之道学说是易学的核心。易学指出,宇宙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天、地、人,称为三才。其中,天地是孕育万物的根本,而人是天地孕育出的最卓越的产物。在天地孕育的基础上,以人文精神,彰显人道的神圣与庄严,体现天道、地道得到充分体现的人文价值化了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充分凸显人在整个宇宙大化中的主体地位,确立人的神圣宇宙责任感与担当感,并推出各种积极的人文举措。由此,人的精神境界也会随之升华,甚至达到与天地、宇宙大化融为一体、毫无隔阂的天地境界,成为“圣之时者”。这一境界的极致,是一种如北宋理学家程颢、明代心学家王阳明所描述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它超越了有机生存、生命共同体下的境界,直接将天地万物视为自身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成就起宇宙式的大我。此一三才之道学说,确立了人在大宇宙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希贤、希圣、希天的人生应然追求,成为主流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
为了实现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易学特别强调将刚健奋进的大有为精神与理性而深沉的忧患意识有机结合在一起,认为刚健而大有所为的人生,富有理性而深沉、长远忧患的人生,才是真正充实的人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在整个大宇宙背景下的主体性作用和人生应然之一切。上述精神与意识,同样成为中国哲学所推崇的基本精神与意识,中华民族也因此成为一个既刚健有为、又深具忧患意识的伟大民族。
易学,是一部“时间的哲学”
所谓“时间的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时间”智慧和视角。它不仅包含了时空的基本含义,而且在时间、空间、事物的一体不分下,用价值的视角,以人为终极着眼点。简而言之,它指的是人在特定时空下,大宇宙和社会人生中各相关因素互动消长的总体格局与状态,以及在此总体格局与状态下的各种事物。
作为一部占卜之书,古经笼罩着浓厚的神秘主义占卜氛围。在哲学理性逐渐显现、非理性神学迷雾逐步消散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通过对古经初步透露出的“时间的哲学”观念的创造性改造与诠释,《易传》升华出了成熟的《周易》“时间的哲学”。
在《易传》看来,《周易》“时间的哲学”,首先教导人们的是明辨时机的意义。
首先,“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从根本上讲,《易传》认为,作为万物中的一员,人首先是一种宇宙性的存在,社会人生的根源在于大宇宙,大宇宙是终极意义上的人的生存家园,唯有以全方位的开放心态,由人的社会放眼其外的世界,人才能开阔眼界,培养并彰显出一种大宇宙心灵,以及一种与大宇宙息息相关、一体不分的意识,并由此为更好地观察、认识与定位自身,以及自身以外的万物,规划人生之当下及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大宇宙层层向下落实,落实到人之为人这一层面,《易传》指出,人又是一种人文的、社会性的存在。而人所处的社会人生,同样是一种感性具体的时的存在。
依《易传》之见,在明辨时机之后,《周易》“时间的哲学”引导人们思考如何把握时机、适应时机,如何把握时机、适应时机而崇德广业,开拓自身理想的生存发展空间。
“时间的哲学”孕育“崇德广业”的人生追求
《易传》认为,按照《易》的理念,由于人道依赖人文的仁义得以确立,人文的仁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价值根基,因此,正大的人生追求,应当是“崇德广业”。即一方面大力提升人的内在形而上的人文德性品位,另一方面以此为价值根基,努力开拓外在功业,以便既能善化他人及社会,又能使社会人生的形而下现实生活品质得到持续提升。《易》正是这样一部圣人用来“崇德广业”的宝典。
在《易传》看来,现实的人生,是置身于一定大宇宙与社会人生的时机之下的。这种时机对其具有不可抗拒的第一位的优先性或先在性,人必然要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地接受既定时机的制约。换言之,对于时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是圣贤还是普通百姓,都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无法自主选择自己希望的时机,也无法轻易让不想要的时机远离自身。在现实的时机面前,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直面它,并适切地回应它。
正因为现实时机的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选择性,《易传》主张,人在保持浓郁的人文情怀与“崇德广业”信念的同时,还应涵养起对现实时机的彻然豁达心境,尽最大可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接受并直面各种现实时机,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泰然无畏地主动迎接各种现实时机的挑战。当迎来较为理想的时机时,不应得意忘形,而应真切领悟到,时机的降临没有固定规律,理想和不理想的时机往往是循环流转的,因此应保持深度忧患并自我警醒;而当迎来不甚理想的时机时,也不应悲观,更不应颓废,而应保持无限乐观的精神,面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易传》称:“真正的君子,在上位时不骄傲,在下位时不忧虑,因此不断努力提升品德与事业,力求抓住时机。”(《乾卦·文言传》)它特别颂扬了生不逢时的真正君子,他们坚定不可动摇的崇高人文德操与心志,称:“不被世俗改变,不求虚名,隐逸世间而不烦闷,不被认可也不烦闷;快乐时就行动,忧愁时就回避,坚定不移,如同潜伏的龙。”
依《易传》之见,人生最理想的境遇,莫过于德、位、时三者的奇妙结合。时机是一种遭遇,职位也是一种遭遇,因此,三者的结合,实际上也可以简称为德与时机的结合,或者德与遭遇的结合。《易传》启示,德、位、时三者奇妙结合的人生境遇,毕竟难得为人所遭遇,人们常常遇到的是等而下之的境遇。
《易传》指出,虽然时机是人无法自主选择、只能承受并面对的,虽然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只能基于所遭遇的时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时机面前完全被动、屈从。恰恰相反,对于现实的时机,人虽然不能自主选择,但可以自主回应。只要采取适当的回应措施,人完全可以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回应,使自己成为能够顺利驾驭现实时机的主体性存在。因此,关键问题就在于挺立这种人的主体性。
挺立人的主体性,以人为中心来审视处理天人宇宙间的一切事务,就是要人从自身出发,拓展出属于自己的人文世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天人之序,达成符合自己价值理念的理想天人关系图景,使自在世界中的存在,化为浸润着人文精神的富含人文价值意义的为我世界中的存在,让世界真正成为为我的世界或属于我的世界。因此,挺立人的主体性,以人为中心来审视处理天人宇宙间的一切事务,也就是挺立人于时机中的主体性,以时机为宏观的大背景,用时机的视野,从时机中万象关系格局的实际出发,由人来自主审视处理一切事务,化自在时机为为我时机或属于我时机,化自在时机中的自在世界为为我时机中的富含人文价值与意义的为我世界,从而达成符合我的价值理念的真正属于我的时机世界。
而要做到这一切,《易传》认为,人需集中主要精力切实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洞悉当下时机的各个环节的同时,总揽其全局,并在此基础上,适切应对、回应之。因此,《易传》称:“上下没有固定规则,不是邪恶的行为;进退没有固定模式,不是脱离群体。君子提升品德与事业,旨在抓住时机。”(《乾卦·文言传》)
适切地应对、回应当下时机,这是一种通权达变的高度人生智慧。拥有这种高度人生智慧,人才能应时因机适遇,开创出最真实且理想的人生德、业辉煌的人生境界。
文章《易学和道教的关系》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对观点赞同或支持。
